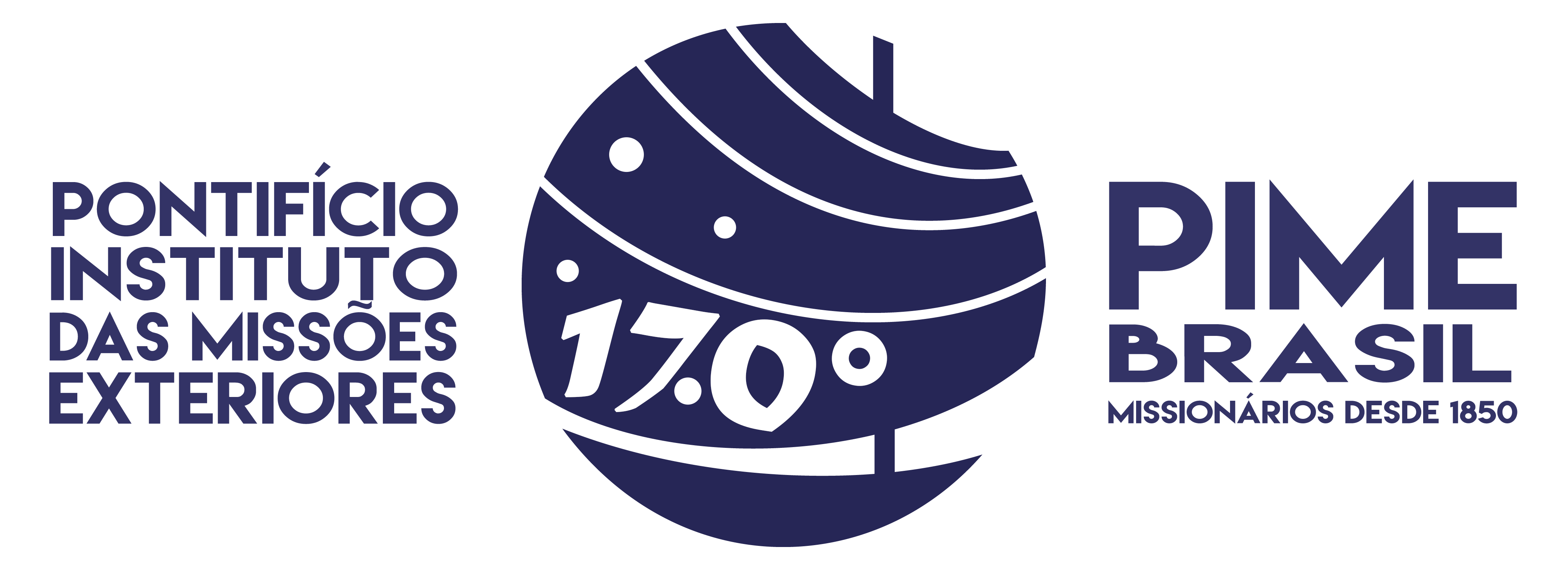帕罗林枢机和塔格莱枢机在乌尔巴尼亚纳大学:“中国教务会议是希望的种子”
乌尔巴尼亚纳大学新学年以纪念1924年《中华公会议》一百周年会议纪要的发布拉开帷幕。良十四世将这一历史性事件誉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里程碑”。帕罗林枢机说:“这条道路交织着现实主义、耐心与信心,即便在艰难时刻也需不断重拾这份信念。”塔格莱枢机说:“这是净化传教工作和意愿的时刻。”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 “中国教会史上的里程碑”。教宗良十四世在致宗座乌尔班纳大学校长塔格莱(Luigi Antonio Tagle)枢机的信中,如此描述101年前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教务议会。昨天,教宗的致辞在本笃十六世大礼堂的新学年开幕式上宣读,并重申了宗座大学的传教使命。在圣座国务卿彼得·帕罗林枢机的见证下,正式发布2024年5月21日在罗马宗座大学为纪念由庇护十一世召集的首届且唯一一次北京会议百年纪念会议论文集。
帕罗林枢机是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支持者。该协议于2018年9月22日签署,并在教宗方济各任内续签了三次,最后一次是在2024年10月,续签了四年。“我想教宗会延续这一路线,”帕罗林枢机昨天下午抵达乌尔巴宗座大学对媒体和《亚洲新闻》表示。帕罗林枢机奥斯定修会教宗采取的措施,包括取消西湾子教区和宣化教区,以及任命王振贵为主教。他补充说,这些协议旨在克服中国“地下”和“爱国”教会的这种“分裂”,并表示“做一个好天主教徒与忠于祖国、为祖国建设和整个社会福祉而合作,绝不会相矛盾。”
2018年的协议是始于1924年上海的历程中的最后一步。这一意义重大的举措——由首位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蒙席(Celso Costantini)发起,主要由非本土传教士出席——“为成熟教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之完全融入中国历史与文化之中”,帕罗林枢机主教在其致辞中表示。换句话说,中国教务会议曾帮助“消除可能与西方政治利益相符的福传模糊性”,指明“逐步但果断地将中国教区领导权委托给中国神父和主教”的路径。两年后,即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为现代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这些初步举措得到了“传教教宗”本笃十五世1919年颁布的《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支持,这封牧函也启发了教务会议。这些努力促成了庇护十二世1958年发布的《致中国使徒的信》通谕,以及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
在2025/2026学年首届学术会议上,帕罗林枢机与信仰通讯社和中国牧灵委员会合作发表了题为“中国教务会议一百周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演讲。帕罗林枢机强调了几个“将上海教务会议与当前旅程完美结合”的主题。他回顾了本世纪初殖民列强对传教士“感人工作”施加的“沉重负担”。这导致了中国人民对福传工作产生“误解”,认为其“是殖民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1924年大公会议很快开始“结出硕果”,强调“所有教会与教宗共融纽带的不可或缺的价值”。枢机继续说道:“当今中国的天主教会呈现出许多特征,似乎回应了教务会议所表达的期望。”
帕罗林强调,中国天主教会硕果累累的历程也交织着“早期的挫折、艰辛和创伤”。然而,这些不应令人恐惧,因为困难“几乎是历史上朝圣教会的构成条件”。他补充说,历任教宗都始终指出“宽恕、和解与合一的道路,以治愈创伤,携手前行”。因此,面对可能“令人失望”的结果,我们必须考虑到——例如——中梵临时协议“这条道路交织着现实主义、耐心与信心,即便在艰难时刻也需不断重拾这份信念”。在艰难时期:一粒“希望的种子”,在禧年尤为重要。“中国天主教团体,如同散落在广阔人群中的小羊群,他们完全融入了国家的现实,与国家共同前行,丝毫不会感到自己是异类。”他如是说。
菲律宾福音传播部副部长塔格莱枢机也与会众分享了一篇充满“传教共同点”的演讲。“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是一次传教大会,”他指出。塔格莱枢机从三点解释了其原因。首先,刚恒毅蒙席的任务是“打开中国新的、不可避免的传教春天的大门”,这通过促进“传教方法的统一”来实现。刚恒毅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充满“传教热情”的演讲,指出公会议的信经应该致力于“传教的普世福祉”和“中国皈依”的共同目标。他说:“归向基督。”
第一次梵二会议有几个“实际”含义,旨在避免帕罗林提到的对传教事业的“错误认识”。其中包括规定“教堂外的文字和标志必须使用中文”,以及“不得出现任何使人联想到其他国家的旗帜或其他标志”。此外,传教士被指示“穿着修道服”,避免“西式世俗服装”。“信徒在传教士面前匍匐”的习俗也被废除。天主教徒也被禁止种植鸦片,这是“西方列强”强加的活动。最后,还规定“任何教会职务都不能拒绝那些证明自己合适的本土神父”。这些举措并非“传教视野”之外的举措,它们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或许更为重要”地实施了本笃十五世1919年发表的《夫至大》宗座牧函。该牧函被定义为“唤醒天主教的一次敲锣打鼓或大宪章”。当代传教事业。”正如刚恒毅总主教所记录的那样,这封信在中国的传教界“充满了不信任和冷漠”。
简而言之,1924年的中国教务会议是“净化传教工作和意图的时刻”,塔格莱补充道,它促成了传教“观念、范式和实践的转变”。这位菲律宾枢机主教补充说,如今仅仅从“主教任命”或“中国政治当局与圣座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天主教会,是“选择性关注,受误导性刻板印象的影响”的结果。它“忽视了庞大而密集的祈祷、礼仪、游行、教理讲授以及牧灵和爱德活动网络,而这些活动往往直接受到伯多禄继承人一般训导的启发”。一种新的“社会和谐”无疑始于上海公会议。他构想了它,并帮助它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