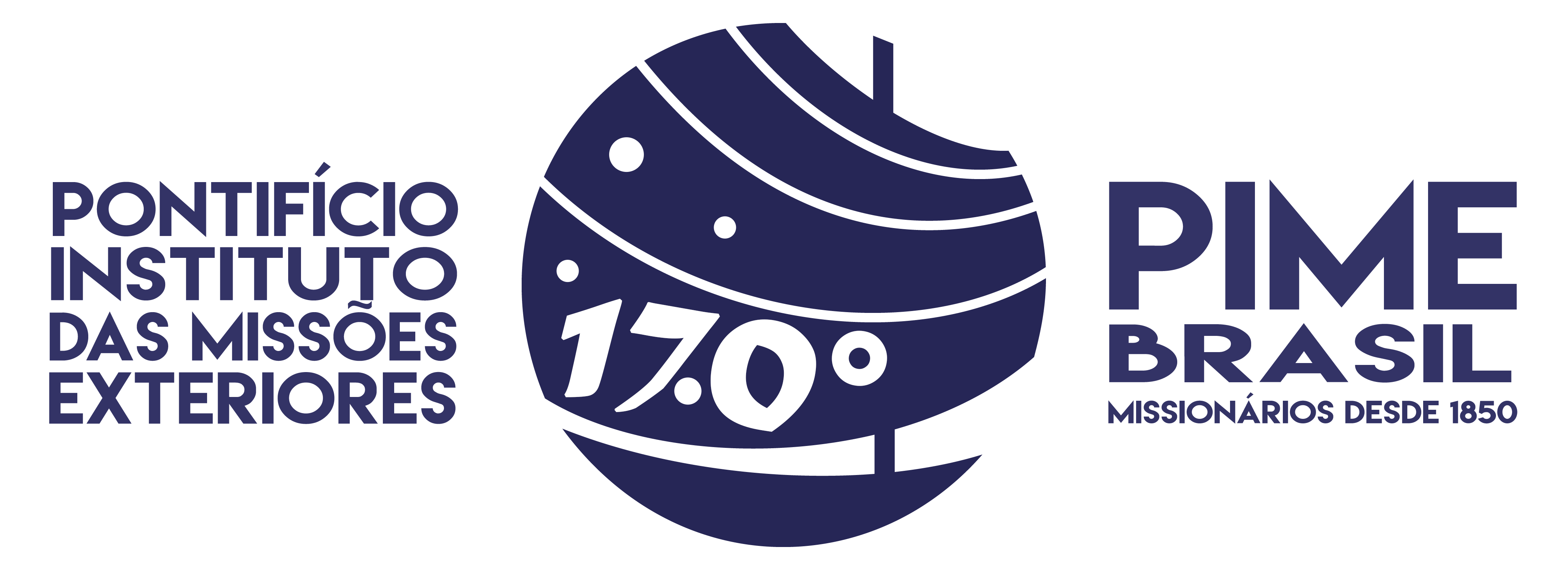普京时代俄罗斯的(被审查的)爱国主义和政治记忆
对不符合国家政策和“传统价值”宣言的出版物的审查制度正在加强。在“苏联枷锁”下被抹去的记忆,任何试图恢复它的尝试都是混乱而虚假的。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目标之一是在民众中灌输真正的“普遍的俄罗斯意识”。回归过去是爱国精神的根本组成部分。
今年1月,一本名为《追寻俄罗斯古迹》(In Search of Russian Antiquity)的书在俄罗斯出版,作者是36岁的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帕哈尔尤克(Konstantin Pakhaljuk)。帕哈尔尤克曾在多所俄罗斯和外国大学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最终却被打上“外国间谍”的标签,被迫在以色列寻求庇护。
在对任何不符合国家政策和“传统价值”宣言的出版物进行日益严格的审查之际,这本书在遭到极端保守的“四十隔离区”运动的谴责后立即下架。
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被指控“亵渎祖国”,但仍有一些副本流入莫斯科的图书馆,并像苏联时代一样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发行,不再用铅笔在桌子底下抄写,而是用手机拍摄。
这位俄罗斯裔以色列作家的“亵渎”实际上在于,他试图澄清关于俄罗斯真实身份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最近的基辅罗斯受洗纪念日上多次重复的正式而冠冕堂皇的声明。
一个关键问题是俄罗斯联邦各省、各百个地区(其中生活着两百个大大小小的民族)的“记忆政治”。 “伟大的俄罗斯历史”的地区究竟“记得”什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它?
“俄罗斯性”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取决于“俄罗斯古代”?帕哈柳克不无讽刺地指出,当前的“Z爱国者”,即支持俄罗斯与全世界开战的人,不太愿意深入探究过去的问题,以避免不确定性和矛盾,因此这项任务必须由一位摆脱偏见和思维模式的“外国代理人”来承担。
历史学家对俄罗斯“新中世纪主义”的看法并非仅仅是为了“回到过去”,让自己沉迷于怀旧情绪和理想化的模式来寻找自身的根源。康斯坦丁旨在拓宽视野,提供一种“去中心化”的俄罗斯历史观,将多种不同因素纳入考量,这在当前情况下尤其重要。
一个对领导阶层和各地方民众的情感影响巨大的因素是,在各种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小民族主义面前,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日益壮大。
然而,帕哈尔尤克并非有意将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而是著眼于真正俄罗斯地区的“俄罗斯性”水平,例如除莫斯科外,俄罗斯中部12个地区,以及斯摩棱斯克、梁赞、大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布良斯克、伊万诺沃、卡卢加、奥廖尔、科斯特罗马、图拉雅斯拉夫尔。
考虑到莫斯科几乎是在所有其他地区之后建立的,那么哪一个地区最具俄罗斯特色呢? “俄罗斯人”这个属性与社会、职业或宗教人物并列: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商人、俄罗斯贵族或俄罗斯东正教徒。这些定义中有许多特别指领土、城市和公国的历史,以及体现俄罗斯灵魂的物品和建筑,从各式各样的克里姆林宫到神圣的圣像,但“俄罗斯人”本身却难以被归类。
在20世纪的“苏联枷锁”下,这段记忆的大部分已被抹去,任何试图恢复它的尝试都显得相当混乱和不自然,以至于在国家言论中,“俄罗斯身份”似乎主要与“苏联身份”重叠,例如沙皇总统兼前克格勃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甚至著名的前克格勃·基里尔(Kirill)大牧首,他似乎经常从礼仪和普京中汲取灵感。
历史的重构常常美化那些从外省崛起、最终在国家(苏联、联邦)中声名显赫的人物,例如伟大的革命人物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他出身于辛比尔斯克南方的资产阶级家庭,更不用说乌克兰犹太人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y)和格鲁吉亚人若瑟·斯大林(Joseph Stalin)了。
毕竟,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的沙皇自18世纪以来就失去了俄罗斯血统的纯正性,而最后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俄罗斯血统也不到十分之一。
回想起来,鉴于俄罗斯英雄们的种族多样性,俄罗斯认同似乎是一种地方主义。最后一位来自西伯利亚深处的真正俄罗斯人是自称神父的格里戈里·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他的姓氏意为“十字路口”,与现任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姓氏“街头人”联系在一起。
正因如此,克里姆林宫现任领导层的意识形态目标之一是在民众中灌输真正的“普世俄罗斯意识”,克服散居在充满陷阱的领土上的民族所特有的分裂感和边缘感,除非被更广阔、更无边无际的投射所主导。
“真正的俄罗斯人”无法忍受被排斥或边缘化;他需要始终感到“处于中心”。
过去十年间,俄罗斯开设了一百多家地方博物馆,不仅致力于战争言论和地方军事英雄,也致力于“融入俄罗斯古代史”的愿望,在地区层面重申了克服国家、联邦乃至全球弱势地位的渴望,或许是透过援引最古老编年史手稿中的一些模糊引文来实现的。
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城市普斯科夫,直到两年前,“帝国史学家”季洪(Tikhon)仍是这里的教会领袖,如今他担任克里米亚都主教。这座城市以其1100年的历史为颂歌,这段历史始于基辅受洗五十多年前,其依据是《涅斯托尔编年史》中的一则记载,其中提到弗拉基米尔大帝(Vladimir the Great)的祖母奥尔加公主(Princess Olga)来自普列斯科瓦,属于普斯科夫地区。
或者,位于俄罗斯中部、拥有超过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雅罗斯拉夫尔,其原型是弗拉基米尔之子智者雅罗斯拉夫王子(Prince Yaroslav)徒手战胜熊的传说。
这些古老而奇幻的故事实际上与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实际发展并不相符,它们的活动和历史存在最多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前,仅仅超过“基督徒千年”的一半。
莫斯科本身在1300年后开始发展,并在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统治下成为帝国中心,而当时“第三罗马”的意识形态并非巧合地传播开来。
这个定义或许是“俄罗斯身份”最具象征意义的定义,它显示了一种渴望回到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帝国的愿望,凸显了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以及他们对自己出现得太晚的持续怨恨。
正如帕哈尔尤克所言,“人为的古化”才是理解当今俄罗斯人以及前几个世纪俄罗斯人的真正关键,他们渴望成为历史伟大价值观的先驱,成为最“传统”、最原创的代表,却不愿承认自己从西方和东方都继承了一切。
这也抹杀了俄罗斯真正的古韵,而这些古韵的见证者包括诺夫哥罗德(Novgorod)、普斯科夫(Pskov)和弗拉基米尔(Vladimir)等地的重要建筑遗迹,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宏伟的克里姆林宫,它俯瞰着伏尔加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15世纪末在首都莫斯科河上建造的克里姆林宫更加壮观。
无需“黄金神话”便可真正理解这些历史见证的价值,更不用说那些可追溯至公元二世纪初的教堂和主教座堂,以及那些由意大利建筑师和工人在莫斯科仿造威尼斯宫殿建造的教堂。
真正的历史认同可以从众多省级中心之间的关系中理解,从欧洲最古老的部分到西伯利亚的亚洲城市,帝国的维度也随之变化,从古老的基辅公国(当时已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到莫斯科-第三罗马帝国和圣彼得堡帝国,模仿着欧洲最负盛名的首都。
在所有地方博物馆,以及层层叠叠的宣传叙事中,“我们失去了俄罗斯”的崇拜蔓延开来,甚至对苏联伟大辉煌的怀念也随着遥远时代的重现而升华,而这种怀念正是当今俄罗斯人意识的真正基石。
尽管正如莫斯科牧首基里尔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抹去记忆的现象,以“西方输入的意识形态”的名义。
回归过去是爱国精神的根本内容,它为镇压“外国势力”和反对摧毁“传统价值”的战争提供了正当理由,目的是为了颂扬一个或许从未存在过的俄罗斯世界,至少它并非像国家宣传的睡前故事中向幼稚的公民们讲述的那样。
【《俄罗斯世界》是《亚洲新闻》的俄罗斯专讯,如欲每周六都收到它,请点击此处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