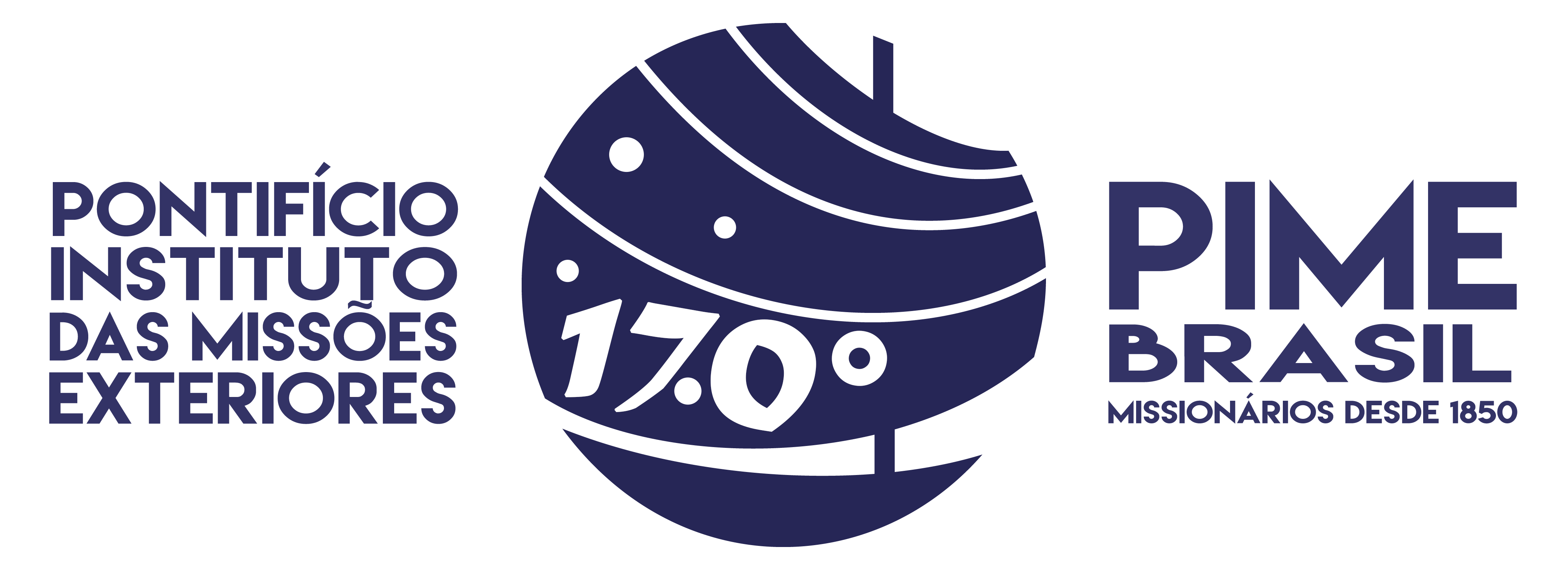俄罗斯的激进新异教主义
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在基督教与异教“双重信仰”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宗教仪式和礼仪实践中,更体现在人们面对人生重大挑战的态度上。这种现象在被派往乌克兰的士兵中尤为普遍,他们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神秘的宗教力量,而非导弹和无人机。
第五届教派研究科学神学会议在莫斯科斯列坚斯卡娅神学院举行,国际演讲嘉宾云集。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斯拉夫异教主义与俄罗斯新异教主义”。会议由该学院的教父学中心、脱离东正教者复辟委员会以及莫斯科宗主教区的其他机构联合举办。2023年,首次就上述主题举办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缘起是,被派往乌克兰参与特种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士兵中普遍存在着神秘主义和偶像崇拜的现象。他们不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导弹和无人机上,反而寄托在邪灵身上,对东正教圣人也置若罔闻。
此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俄罗斯各东正教神学院、联邦各地区与希腊公立和私立大学的众多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开幕致辞由圣彼得堡普希金国立大学宗教与民族政治研究中心哲学家罗曼·希任斯基(Roman Šiženskij)发表,主题为“东正教中的俄罗斯异教:传统与创新”。随后,神学家罗曼·孔(Roman Kon)作了题为“东正教与本土宗教中的民族性和爱国主义主题”的报告。
由于新异教主义与军事行动的关联,该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凸显了“战争宗教”中异教化的倾向,而东正教宗主教区对此尤为重视。这实际上是追溯至罗斯基督教起源时期的一个维度,当时基辅人民在王子弗拉基米尔的命令下接受洗礼,仪式是在将所有异教偶像投入第聂伯河后,通过浸入河水来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古老宗教与新兴宗教的思潮在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交融在一起,他们始终生活在基督教与异教“双重信仰”的张力之中。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宗教仪式和礼仪实践中,更体现在人们面对生活巨大压力、饥荒和自然灾害的态度,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入侵和侵略等诸多内外冲突中。
基辅罗斯的文学杰作当属《伊戈尔的军队之歌》,它讲述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子之子于1185年率军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悲惨战役。这是在鞑靼-蒙古大军入侵前几十年,为保卫领土免受外敌侵扰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这首诗由“诗人博扬”叙述,思绪沿着树干蔓延,地上是灰狼,云下是蔚蓝的雄鹰。除了对自然、植物和动物的精彩描写之外,这位诗人激励罗斯的子孙们,在库曼战场的边缘折断长矛,并以此为灵感来源,效法博扬——这枚"远古时代的夜莺",他是韦列斯的后裔。韦列斯是古神之一,其名衍生出"弗拉斯"(Vlas)一词,意为"权力",而这正是"弗拉基米尔"(Vladi-mir)名字的根源,寓意"掌控世界"。这个名字从第一位大公到末代沙皇都极为盛行。
歌中展现了所有源自斯堪的纳维亚、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偶像。迪夫(Div)振作起来,敦促他们聆听苏罗日(Surozh)、科尔松(Korsun)以及你——特米托罗坎(Tmitorokan)的偶像——的教诲,以抵御达日德博格(Dazhd'bog)军队的进攻,并提及一系列其他神话人物,包括伟大的乔尔斯(Chors)和佩伦(Perun),这位战神两百年前沉入第聂伯河,但不断复活以“重燃战火”。伊戈尔王子在与来自亚洲的波洛茨基人的战斗中战败,苦难蔓延至整个俄罗斯大地。基督教随后才传入,最初是来自异域的赞颂,德国人、威尼斯人、希腊人和摩拉维亚人齐声歌颂斯维亚托斯拉夫,哀悼伊戈尔王子,直到故事的尾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才在清晨的波洛茨基为他响起,即使身处基辅,他也听到了钟声,尽管他那具双重躯体中寄宿着一位魔法师的灵魂。史诗最终以道德上的胜利告终,尽管他战败了:太阳照耀大地,伊戈尔王子回到了俄罗斯大地,走上圣母玛利亚的圣殿。向那些为基督徒对抗异教徒而战的王子和战友们致敬!
这些古老的诗歌灵感,俄罗斯人即便在失败的战争中也引以为豪,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与鞑靼人的战争到与波罗的海诸国、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甚至在战胜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战争中,尽管数百万俄罗斯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仍然宣称取得了永恒的胜利。如今,这种“光荣的失败”在乌克兰战争中再次上演。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反而宣称“传统价值观”战胜了西方异教徒的堕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继2025年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之后,普京总统宣布2026年为俄罗斯各民族团结年,同时缅怀“苏联人民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追溯历史至《伊戈尔的盛宴》,这场悲剧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也阐明了俄罗斯人民对远近各国人民的伟大之处。
基督教与异教信仰相互交融的现象并非俄罗斯东正教独有,它贯穿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及更广阔地域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古代教会逐渐吸收并“净化”了基督教信仰,使其融合了古希腊罗马和东方的各种宗教元素,并通过大公会议来界定正统教义的范围。然而,俄罗斯人却经历了先辈传统与新兴宗教机构并存的局面,未能将二者的差异在信徒心中确立下来。以至于如今,印有“我不是天主的仆人,而是祖先神明的继承人”标语的T恤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
异教崇拜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蔓延长期以来一直未被察觉,仅在东正教会偶尔对俄罗斯各地的地方性节日和狂欢活动提出零星批评时才有所显现,这些批评从“祖先的宗教”到“破坏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不等。2021年,宗主教区负责社会关系的代表瓦赫坦·基普希泽(Vakhtang Kipšidze)表示:“据我们所知,新异教主义现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我们看不到任何能够将新异教徒团结起来的共同点。”这正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尽管随军神父们致力于“净化”和颂扬战斗人员。总的来说,提及基督教洗礼前罗斯地区盛行的宗教似乎相当牵强,他们使用明显不可靠的资料来塑造一个更像是电影角色而非古代宗教典籍的神祇体系,这些神祇佩戴着护身符,身着怪诞的服饰。
一些新异教倾向推崇自然主义,反对高度科技化的文明,提倡“回归本源”,追求自然和谐,正如古代诗歌《伊戈尔》或托尔金笔下的侏儒、精灵和霍比特人的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宗教史学家阿列克谢·盖杜科夫(Aleksej Gajdukov)指出,“异教是基督教用来指代非亚伯拉罕宗教的术语,而新异教或新异教则是一种当代现象,它恰恰是在所有宗教传统中断之后发展起来的。”古代异教习俗和信仰的传承在第一个基督教千年中被遏制并废除,但俄罗斯在第二个千年前夕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却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长久地保存了这些习俗和信仰,以至于它们甚至在苏联无神论时期仍然存在,而苏联无神论本身最终也类似于一种异教。
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国家东正教的推行催生了各种形式的异教倾向的激进主义,从那些声称“我们不像基督徒”以彰显自身独特性的人,到那些证明“我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超级东正教僧侣,不一而足。我们还记得前修道院院长谢尔盖(罗曼诺夫)的故事。2020年底,他在斯列德涅乌拉尔斯克的修道院被捕。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反疫苗教会”,拥有150名修女。这些修女无视所有防疫限制,在树林里跳舞,自诩为“末日先知”,并敦促信徒们抵抗“反基督势力”。他将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也列入其中,认为基里尔传播新冠病毒是为了“抹去人们心中的神圣形象”。
压垮民政和宗教当局忍耐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谢尔盖的一段布道视频。在视频中,他询问一些信徒,包括一些孩子,是否愿意“为俄罗斯而死”,并明确呼吁他们自杀。而如今,正是基里尔宗主教呼吁人们为战争的胜利祈祷,宣称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对抗乌克兰境内的西方反基督势力。新异教主义以仇恨和暴力取代对基督的爱,而普京和基里尔两位弗拉基米尔统治下的俄罗斯,实际上又回到了崇拜韦列斯——那个毁灭世界的权力之神——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