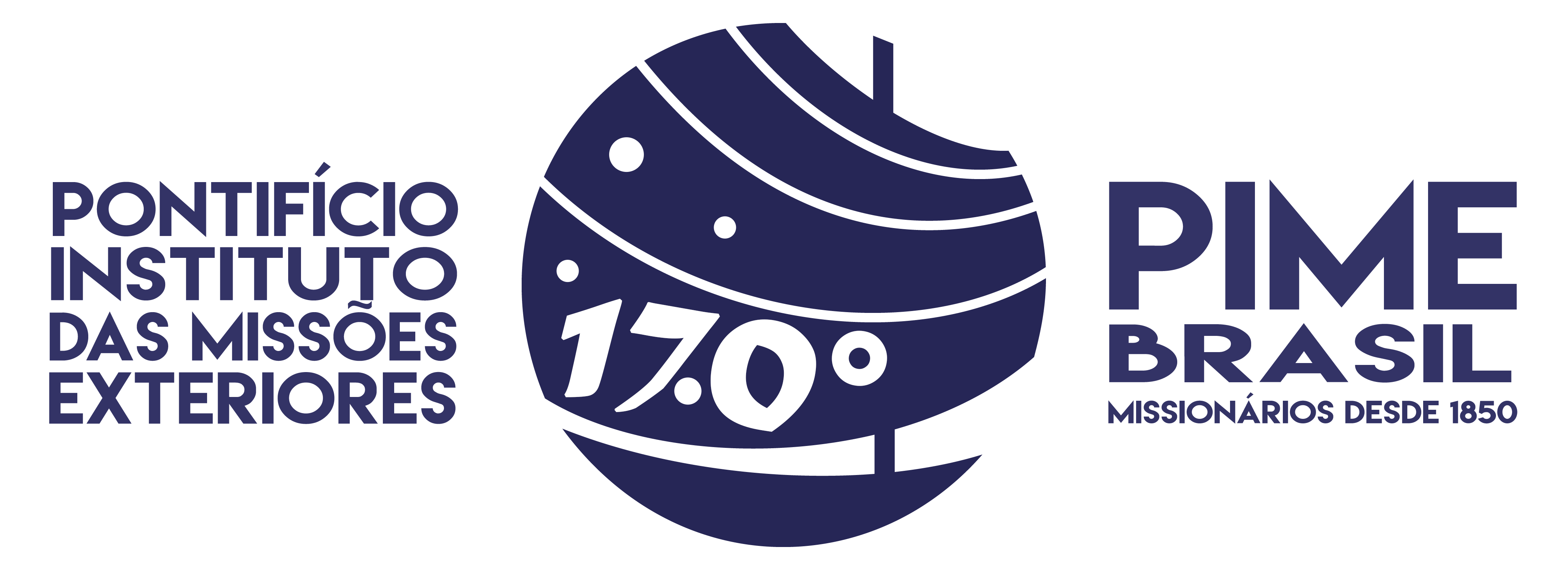普京治下俄罗斯的罪恶感与新野蛮主义
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的最新作品在布拉格发布。叶罗费耶夫是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一直批判俄罗斯战争的作家。压抑罪恶感已成为一种本能。苏联解体,东正教教会从未就与无神论政权合作道歉。赫鲁晓夫曾预言俄罗斯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动战争,反对派在海外的失败。
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Viktor Erofeev)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自2014年以来,他一直居住在柏林,并对克里米亚吞并后克里姆林宫的侵略政策持反对态度。此次,他在布拉格发布了最新著作《新野蛮主义:一部关于俄罗斯罪恶的小说》。它既是对当代俄罗斯人意识及其历史和心理根源的反思,也是对如今日益重要的、构成我们生活节奏的民族永恒本质的反思——“俄罗斯灵魂中永恒的野性,永恒的野性”。
叶罗费耶夫以一个关于祖母杯子的寓言故事开篇,这个杯子象征着俄罗斯的性格特征:“我的祖母,阿纳斯塔西娅·尼坎德罗夫娜(Anastasia Nikandrovna),是一位面色红润的美人,但即使是美人,有时也会打碎杯子。”那只蓝色的杯子从她手中滑落,掉在厨房的地板上,摔得粉碎,只剩下断掉的把手,孤零零地躺在角落里,毫无用处。祖母从未说过:“我打碎了一个杯子。”他是这样说的:“杯子碎了。好像杯子会自己碎掉似的。当然,它也可能意外碎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仿佛看到我的祖母绝望地、怒火中烧(她脾气暴躁),故意打碎了杯子,但我无法想象她会道歉:“是我打碎了杯子。”
这只破碎的杯子代表了俄罗斯的罪恶感,以及对罪恶的断然否认,或许是因为在俄罗斯,犯罪的惩罚从来不与罪行成正比,而是总是更大,“就像面团从锅里溢出来,溢出到世间一样”。在贫困家庭里,杯子是珍宝,“贫穷是俄罗斯的罪恶;如果我毁坏了一件家传珍宝,我就犯了家罪,要为此受罚,但我买不起新杯子。我没钱。我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或者推卸给杯子本身。它从我手中滑落,摔碎了。”这个寓言表明,压抑罪恶感已成为俄罗斯人的本能:因为打碎了一个杯子,他们可能失去一切。打碎杯子的指责会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难怪“总是”和“从不”这两个词在俄罗斯人的日常对话中频繁出现。比如,“你吃饭前从来不好好洗手”,“你从来不跟我这边的亲戚打招呼”。
没有人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军方。弗拉基米尔·普京经常重复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搞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谁想在“星球大战”中超越西方,是谁入侵阿富汗,引发了无休止的怨恨和复仇,最终导致了激进伊斯兰运动、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袭击、ISIS战争等等。东正教会拒绝为其与无神论政权的合作道歉。该政权利用东正教会麻痹少数残存信徒的良知,并在国际上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东正教会从自发的宗教复兴中攫取了新信徒的良知,将他们重新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就在不久前,基里尔宗主教还吹嘘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莫斯科一样,在建教堂如此之多”,而如今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去教堂只是为了支持战争。
叶罗费耶夫认为,“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他人是俄罗斯人的全民爱好,因为强者不愿道歉:为打碎的杯子承担责任是徒劳的。”这位作家属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后现代主义”一代,他们用乌托邦式的意象来描绘现实,这些意象着眼于过去,而非科幻式的未来。早在1982年,他就与概念主义作家德米特里·普里戈夫和“普京主义先知”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Eps”的文学团体,该团体名称取自他姓氏的首字母。索罗金于2006年出版了《奥普里奇尼克日》,这部作品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俄罗斯政治的走向,将普京描绘成奥普里奇尼克首领、伊凡雷帝的卫兵、残暴的马柳塔·斯库拉托夫等等。如今,俄罗斯人恳求他不要再创作这类小说,以免现实远远超越幻想。
这位作家与那些渴望“走向公众”的记者截然不同,他更倾向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那里可以批判一切人和事,因为在房间里他是自由的”。这种状态可以追溯到苏联地下出版物时代异见者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如今又日益凸显。叶罗费耶夫的父亲曾是斯大林的翻译,因此后来被派往巴黎担任外交官。小维克托在巴黎长大,坚信“欧洲是我的家,是我的自由空间”,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俄罗斯身份。正是这种信念,构成了他作为作家的本质,他并非“想要写作,而是想要体验每一种情感……作家是天生的,而非后天培养的”。
1975年,他以一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法国存在主义》的论文毕业,这篇论文在苏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2岁时,他的第一篇论文《萨德侯爵、虐待狂与二十世纪》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审稿后发表于《文学问题》杂志。该论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其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虐待狂的一段话。回忆起他在欧洲和苏联的经历,叶罗费耶夫指出,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自由远胜于普京统治下的自由,因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不再有任何建设共产主义的努力,而是共产主义为高级官员建造了豪华住宅。”然而,如今“我们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我们甚至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或许只有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还能与之媲美。”在《瓦尔瓦斯特沃》(Varvarstvo)——一本探讨俄罗斯野蛮行径的著作——之前,他曾著有《大流氓》(Velikiy Gopnik)一书。书中,他借用苏联时期“流氓”(gopnik)一词的定义,将普京总统比作“我们这个时代日益普遍的愚蠢,正是这种愚蠢滋生了我们所处的野蛮世界”。流氓们使用粗俗无耻的语言,就像普京一样。普京最近指责欧洲人是“拜登宫廷里的猪”,并声称俄罗斯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没有文明,只有腐臭的堕落,”他在12月19日与民众的“热线”节目中反复说道,甚至还回答了孩子们的提问。
另一方面,野蛮行径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从古希腊时期到罗马帝国的解体,如今,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极端自由主义文明的末期,野蛮行径以“绝对且普遍”的方式重演。在此,作者指出了“俄罗斯的罪责”,认为正是俄罗斯开启了野蛮时代,而其他所有民族如今都在适应这种野蛮。小说中,“俄罗斯的罪责”被拟人化为一位32岁的年轻女性(后苏联时代),即叙述者的妻子,她“毫无逻辑地表达爱与恨”,这个人物体现了当今俄罗斯人所处的噩梦。
小说让人想起1953年格鲁吉亚独裁者斯大林去世时,他的继任者、乌克兰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向民众发表讲话,呼吁“至少让我们尽量不要互相残杀”,这番话预示了近期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当时,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历任党领导人都试图展现一些人性,而如今,“时间正在与我们作对,我们只能希望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能够尽快结束。”人们常说“希望是最后消亡的”,而叶罗费耶夫却认为,在俄罗斯,“希望最先消亡”。就连如今互相争吵、互相谩骂的国外反对派,也早已不再代表真正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但话说回来,“在法国或其他地方,也看不到真正能够拯救世界的知识分子阶层。”
尽管如此,叶罗费耶夫仍然坚信“俄罗斯还没有消亡,因为俄罗斯如此庞大,不可能彻底消亡。”没有人能够预知战后俄罗斯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战争最终结束,或者至少停止——而普京绝对不希望战争结束——但就像苏联解体时一样,“没有人会为已经发生的灾难承担责任;我们都将成为一张白纸,任人书写新的篇章。”